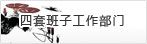西风散板听离歌
来源:
作者:
发表时间:2021-03-15
西风散板听离歌
何恩鸿
北江自北来,到这里折而向东;西江自西来,到这里折而东南。
北江依城而过,静水深流,进入河网密布的三角洲地带,名称再经替换就成了珠江。说是珠江,不是很确切。珠江既是北江流至广州后的名号,也基本上是整个岭南水系的统称。珠江有七大入海口,西江奔流到珠海入海,也统称珠江。难以界定、波澜不兴、沉静错综的珠江是岭南文化最好的隐喻。
这些复杂的交错与名称的流变,大致都是以这里为起点。这里两江交汇,这里大河奔流,这里叫三水。三水三水,那么还有一条奔流的江水呢?众说纷纭之外,我更愿意理解为古人诗意的想象。当然,想象之外,一定存在着或存在过一条称得上江的河流,相信它并不在我们的眼界之外,只是在我们的意识之外。主流的说法是那条江叫绥江,也有人说叫肄江,还有人说叫胥江。这些名号同样有着难以名状的诗意。一条存在着或存在过的河流,名称如此众说纷纭,也是很有诗意的事。
这里有很多诗意。比如汇流处正对江心的那座仅62米高的小山,它叫昆都山;两江汇流的水道,它叫思贤滘。对不了解掌故的过客而言,它们也许只是名号,甚至名不副实;对奔流的江水而言,他们是见证,见证着时光流淌,沧海桑田;对知悉这片热土的人们而言,它们是厚重的史录,铭记了波澜壮阔的春秋。昆都山下,唐代始设三水司,肇始三水之名。八百年后,三水成了这片息壤的个性徽标。
汇流处,五百年前有座城池,名字特别朴实,就叫河口。三水建治开埠就在河口,这里一度商贾繁华参差数万人家。风烟漫卷,朝代兴替,人们渐行渐远,向东迁延,慢慢扩展为一座新城,这座新城当年叫什么名字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可知的时候,它就叫西南。珠三角核心地带或者说起点,三水首府,八方通衢——西南,南方的西南,一座滨江小城。得风气之先,处交通之便,经济发达,人口富集,但也只是不到三十万人口的现代小城。珠三角的小城大多都有个诗意的名称,如南海的桂城,顺德的凤城,高明的荷城。三水的府治所在的这座城市有些莫名其妙,就叫西南。这里的一些雅人可能实在不忍,就别名淼城。这个名字明显是小文人的得意之作,也就难为大众所广泛认同。大家还是一如既往地称之为西南。
西南何以得名?源自何时?查证稽考,莫衷一是。有人说是因为曾经隶属南海郡或广州府,这里处在西南位置,这种说法明显牵强。因为西南以前并非治所,也非要冲。百年前,这里也许还是小小渔村,难以那般受待见。而且,三水还是西南都并非在南海或广州的西南。另有一考证认为,古时广州到肇庆的驿道途经此地,有个驿站。驿站的西南角有个墟集,叫西南墟,名自隋朝始,至今一千四百年。这或许才是西南称谓真正的源头,大概只是因为年代久远又无书典记载,以致湮没无闻。
十二年前,学孔雀东南飞,飞到处正是此处的西南,一个名实错综而又意兴款款的地方。西南,字面上给人遥远偏僻的感觉。事实上,这里的市井人生也确乎有偏安一隅的安静闭塞。小格局,小日子,小情调,小精明,小算计,小嘚瑟,过着小心翼翼的庸常人生。大家固守着三千年前孔子推崇的雅言传承而来的白话,陶醉于文火慢煲的老火靓汤;悠悠地叹茶,慢慢地剔牙;家家供奉着神龛,遇事烧纸拜佛;很多人的口头禅是“我丢”,乐此不疲的工作是“吹水”,津津乐道的盘中餐是“龙虎”……日头升起又落下,落下又升起,人生就在驿道边慢慢老去。这种别样的景况,虽非诗意的栖居,也可为一种静谧闲适的人生,虽然当初三千里追寻的皈依般执着与如今为稻粱谋的现实有着巨大的反差,以致偶尔也会升腾起某种形而上的感伤。
西南离离,江水悠悠。
所有选择都理所当然,我相信西南于我是偶然的栖居,也是必然的宿命。我明白,人生很多所谓的意义,都如路的尽头仍然是路的顺理成章。面对大自然,我有无尽的自在与喜悦;面对城市与人群,我有无言的寂寞与空虚。相较而言,我喜欢西南这样的小城:它喧嚣也沉静,它张狂也本分,它开放也内敛,它贫乏也富庶,它尊大也卑微。生活于其间的人们,很多得意的浅薄,很多封闭的固执,西南的格局不会放大它,也不会消弭它。这个城市日新月异,又固守很多陈规陋习;这里少见戾气,也少见精细;不回避粗俗,也不追求风雅;没有多少是非曲直,也没有多少成败得失,它就是北江水的随波逐流,波澜不兴;也正如离离荒草的春荣秋萎,花开花落。
很多事,很多理,就像臭豆腐,看不得闻不得,吃得品得。人生降格以求,自在便是安好。执着追寻,总难免迷在其中。西南是个小城,骑单车不用一小时就能贯穿,但是我依然常常迷失在春花秋月的各个出口或入口。我从哪里来,应该说大致明白了;我在哪里,也似乎没有多少疑惑;我要到哪里去,这个问题总让人困惑不已。生活在这样的小城市,正如生活在体制之中,言行稍有不慎,就跨越了边界,甚至穿越了时空,生命的本能教会了大家雾里看花,迷失也因此成为一种人生常态甚或正态。这里的迷失也因此基本上与方向无关,只与小聪明有关。
方向上的西南,伏羲八卦在巽,文王八卦在坤,这是风吹大地、鲜花盛开的意象。曾有人说佛山无山,西南这座城市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山岳高丘。大地茂盛,四时花开——这样描述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恰切的。《诗经》有云:“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这首诗谓我心忧,我很喜欢。可是,茂盛的大地,为什么是家国的忧伤?年少的当初,读到这样的诗句,很难感受到文字之外的况味。现在懂得了,却少了当初读诗的那份情怀。也好,不用为赋新诗强说愁。现在也很少读诗了,但惯性使然,依然在追寻。追寻什么,自己似乎也不清楚。先天八卦中,南方为乾卦,乾为天;后天八卦中,南方为离卦,离为火。北回归线横穿三水,西南在北回归线以南,是真正意义上的南方。五行中,我喜水不喜火。这里是离火的南方,这里也是三江汇流的大地。常言水火难容,玄门中却有水火既济之谓,贵在中和。离离之火,浩浩流水,三水大致可以算得上水火既济之地,我的小日子虽然没有因之风生水起,小得瑟也是可以的。
训诂上的离字也等义忧伤。离忧,三千年古风的长调,从孔夫子逝者如斯的慨叹到屈子怀沙的沉郁,从太白对影成仨的孤楚到东坡水调歌头的悲怆。这些与史同庚的知识分子,需要投入、表态、传播;今天的我们,感受到的却只是他们那比风还轻的离绪忧怀。有道是,使人疲惫的不是远方的高山,而是鞋里的一粒沙子。常言岁月如歌,现实的人生则往往是心中有高山鞋里也有沙子,很多各不相干的事,因为观念、心态,因为机缘种种,如风声、雨声声声入耳,历练而成生命之歌。爱恨情仇,得失成败,都是歌的内容;西风猎猎,流水汤汤,都是歌的曲调。在我的视听里,《离骚》是屈子仰天长啸的离歌,《归去来兮辞》是陶氏辗转反侧的离歌,前后《赤壁赋》是苏子洞明世务的离歌。这些伟大的形制,是皎皎明月照彻黑夜,是丰赡大地水流花开,是猎猎长风吹散阴霾。生命是时间的长河,我的河流至此迂回,终将流向远方。此时的此处,很好地契合着元人张可久“人老去西风白发,蝶愁来明日黄花”那久远的感伤。
吃是岭南文化自得的招牌,也是传统中国自诩的精髓,我们都是饕餮吃货。可是,要选出西南美好的吃品,真真乏善可陈。唯一能被大家认可的竟然是一种叫臭屁醋的小吃。这种小吃在正规酒店买不到,只在僻街陋巷才有,而且在整个三水,现在似乎只有西南的一两家小店有卖。女人生孩子的喜庆,则是一定要给同事乡党呈上这种吃食的。黑乎乎的,陶罐装着;甜丝丝的,热热喝着。吃得到,难买到;没品相,好味道;名字鄙俗,营养丰富:臭屁醋是西南最好的隐喻。
新年到来之际,这里都会请到世界顶级的交响乐团演出。我也曾多次隆重地去捧场,事先都会被正告正装、鼓掌等行止。可惜我的耳朵无法被正告,浸淫民乐太久,它只喜欢沉郁温婉甚或凄怨迷蒙的丝竹呕哑。然而我听不懂粤曲星腔,这可是三水难得的风雅乐事。粤曲传人小明星是三水的骄傲,她始创的星腔,打破传统程式,独树一帜,是艺术成就最高、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粤曲唱腔流派,至今传唱不衰。发生在故乡古皖大地的小城故事《孔雀东南飞》也曾被演绎成星腔名曲,这是件值得激动的事,可惜我依然听不懂咿咿呀呀的爱恨情仇。我喜欢汉乐府的《孔雀东南飞》,这是一曲感天动地的离歌。也曾努力去欣赏粤曲星腔的《孔雀东南飞》,因为不懂,无法入戏。感觉两者完全风马牛不相及,但是,只要有雅兴,在西风泛江的晨昏,独处西南一隅,置清茶一盏,听一曲星腔散板横陈爱情史诗,也是人生一乐事。
“满载一船明月,平铺千里秋江。”古人真好兴致,是我学习的榜样。新年又快到了,这个新年,于家国有很多刻骨铭心的记忆;于我个人,则有春暖花开的美好寄寓与期待。我给即将到来的新年拟了副对联:甲秀锦云鸿有信,马跃春山雁传音。这是对新年的期许,也是对当下的想象。南方之南,从气象学、物候学的角度看,春天是没有的,鸿雁也没有。